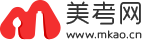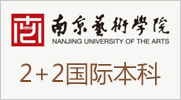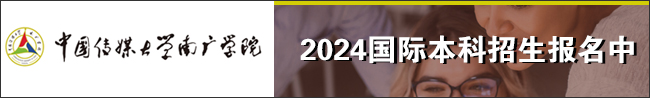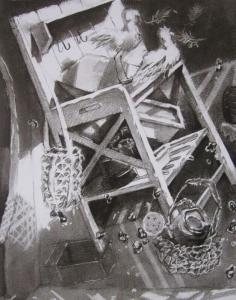一个多世纪以前,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,自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,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就成为世界性的了。物质生产如此,精神生产也是如此。这样,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就成了世界公共财产,许多民族文学和地方文学也就成了世界文学。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话,即使在时人听来,也会感觉不舒服,因为那时很多人不希望它变成现实。可它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,尤其是在电影、文学、舞蹈、音乐等领域。谁会否认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力呢?但对于现在的中国画坛来说,“世界美术”这一称谓实属危言耸听。虽然世界各民族的美术相互影响已是客观事实,且还涌现出许多东西合璧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西方美术家,但类似的中国画家出现得却不多。
“世界美术”之于我们仍是遥远的梦想,但并非遥不可及。如此泱泱大国自然应该奉献给世界几位这样的大师,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。随着各种国际美术双年展在中国的启动,各国美术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。这为中国能出现几位中西合璧的绘画大师提供了可能。这一点,在2003年、2005年的“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”中已露端倪。但是我们在潜意识里大多不愿让它变成现实,因为美术圈,尤其是国画圈、书法圈对中西合璧有着十足的警惕与戒心。特别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,有些人会打着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”、“保护多元文化”的幌子堂而皇之地阻挠这一进程。
不可否认的是,再超脱的画家也乐于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。但很多画家在享受这些成果的同时,却又不愿看到艺术被现代化。这大多是他们的一厢情愿。他们沉浸于笔墨游戏中,沾沾自喜,却没有注意到观众冷漠的表情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经济基础改变了,上层建筑迟早要变。艺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,虽在上层建筑中离经济基础最远,但也不例外。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,艺术必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共融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全球经济的一体化、现代化首先带来生活方式的趋同和审美心理、审美趣味的趋同。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艺术的一体化乃至剧变,因而企图阻止艺术一体化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徒劳,除非社会倒退到“长袍马褂”的时代。艺术除了具有民族文化内涵外,还是一定的生产力、生活方式的产物。所以,一种艺术虽诞生于西方国家,但并不意味着它只属于西方国家,它向东方国家传播也不一定就是文化的殖民主义。即使我们现在不接受这种艺术,等我们的生产力、生活方式达到一定高度时,也会产生类似的艺术形态。
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、社会生活的现代化(不可否认的是,目前任何现代化都与西方有关),中国许多传统文化、文化遗产濒临灭绝,传统水墨也受到了很大冲击,观众大量流失。尽管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传统水墨复兴的迹象,而且似乎非常引人注目,但这多半是圈内的事。现在,除个别的大型展览和一般的美术展览开幕当天有许多人参观之外,其他时间大多寥寥无几,出现了“开幕即闭幕”的现象。一些新兴的艺术展览“夺走”了一部分观众,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但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,美术高考逐年扩招,现在大学里广泛设置了艺术修养课,一些院校甚至在非艺术类专业中增设了美术创作选修课,应该说培养了更多的美术观众;可实际上,还是没有多少人去看美术展览。关注美术的观众基本来自圈内,而关注其他艺术门类的观众主要来自圈外,这就使得美术创作多少带有“自恋”的性质。国画创作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除教化功能和美化生活外,绘画还有四种功能:记录历史,改变人们看世界的眼光,改造社会,抚慰心灵。具体来说,其一,不管是直接或间接,绘画或多或少都会记录画家所处的时代生活。其二,绘画通过它所塑造的形象改变人们看世界的方式。杰出画家的能力在于能敏锐地感知到社会和公众的心理变化,并能找到一种有效的视觉形式来揭示这种变化。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“混搭”时代,那么这一时代则是由毕加索立体派绘画开启的。其三,绘画可以不通过美化和教化的方式影响生活、改造社会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处处存在着“设计”的时代,而这与“冷抽象”绘画的诞生密切相关。其四,中国画创作主要是抚慰心灵。在这里,时间仿佛是凝固的,画家似乎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因而绘画流于“笔墨游戏”中。在当代,这种状况比清代“四王”之后的画坛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现在山水画的创作多是千篇一律的古人图式,残山剩水、茅屋渔樵、庙宇寒僧、木桥帆船,作品没有一点儿时代气息。如果说国画有记录历史的功能,且中国不缺绘画大师,那为什么迄今为止,中国画坛还未出现一位像毕加索一样能够改变人们看世界的眼光、像蒙特里安一样将绘画广泛渗入生活中的绘画巨匠?或许可以说,这正是画家“自恋”的创作心态所致。